
作为Thrash Metal(鞭挞金属)的先驱者,Metallica迈出了奠基的第一步,也因此将地下音乐最大程度地引向公众,一步步成为史上最成功的殿堂级重金属乐队。
http://gslb.miaopai.com/stream/tQWHoeO4n2ey8EwahRmcOJccksp~LBWPiSU0OQ__.mp4?vend=miaopai&ssig=f2922b29d9416cd558566ee987b3e022&time_stamp=1545637965984&mpflag=32
http://gslb.miaopai.com/stream/tQWHoeO4n2ey8EwahRmcOJccksp~LBWPiSU0OQ__.mp4?vend=miaopai&ssig=f2922b29d9416cd558566ee987b3e022&time_stamp=1545637965984&mpflag=3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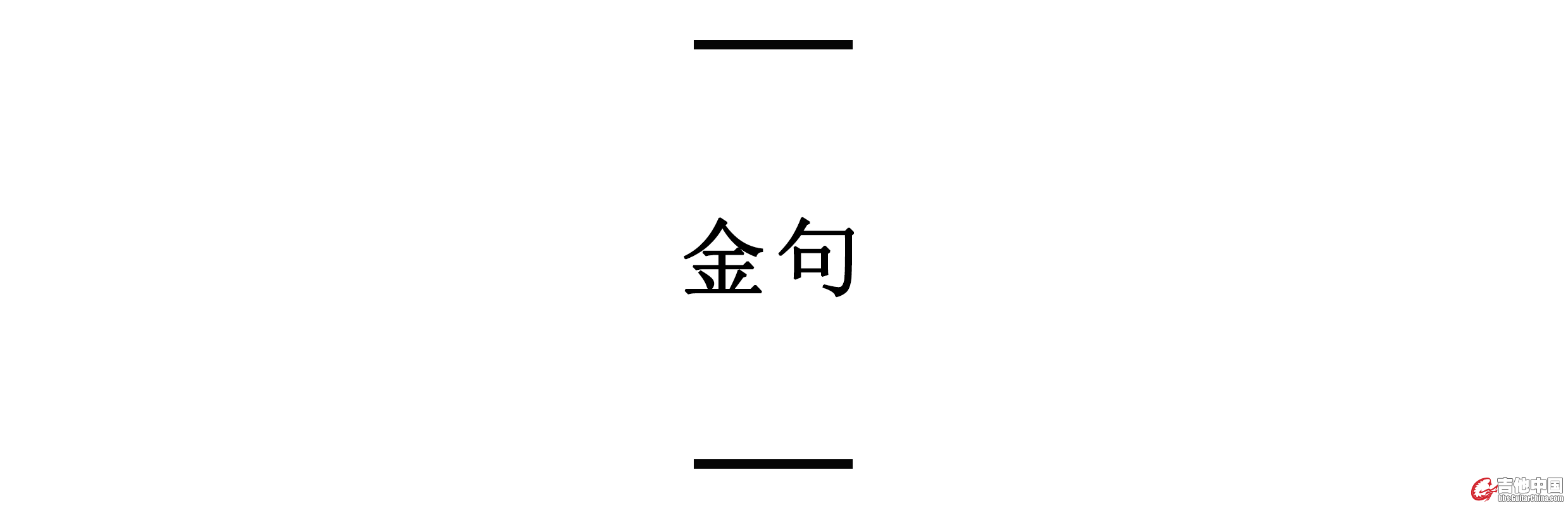
1. “重金属”这个标签,对我们来说,一直都有点太局限。重金属的乐迷曾经对我们很生气,因为我们经常不按规矩出牌:把头发剪短了,不穿重金属乐队应该穿的那种服饰,忽然间出了一首抒情慢歌“Nothing Else Matters”—— 哇,乐迷都炸锅了:“不要不要不要!”我们不在乎,真不在乎。我们的音乐是为自己写的,这是天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所以我们算是叛逆者中的叛逆者吧。 2. 黑暗将会是我们永恒的主题。我们喜欢做的是在漆黑之处洒下光芒。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,我喜欢去照亮黑暗的角落,但有时候它还是会袭来。许多Metallica的乐迷,或是出于恐惧,或是出于对家人和朋友的需求而对我们的词产生共鸣。联系人心是最重要的事。我把自己怎么想的写到歌里,外面听到的人也有共鸣,同样是在社会中格格不入的人,便不再感到孤独。 3. 我一向以来都被重金属或者说重型摇滚所牵引,我知道外面有些乐迷跟我们是一样的,因此我们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而“重金属”这种音乐,至少在美国,人们总是认为是年轻人的音乐;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了。我们一直都在进化,在成长,在改变。进化很重要,我们现在的音乐肯定跟1983年的时候不一样,我是不会一遍一遍去画同一幅画的。 4. 在《火中飞蛾》里,我写到了“名气”之下的众生相。包括美国人一项著名的消遣:先将你捧上天,再把你乱刀砍倒,看着你从高空坠落,真是精彩得没朋友。又或者是削尖了脑袋要把别人家长里短打听个一清二楚,好装成道德义士去指指点点。在各种艺术领域里,像Amy Winehouse这样的遭遇已经重复上演了无数次:你追寻的是明亮而真实的人生,但人们将你捧到了一个不可能的高度;于是名气逐渐毁掉了自我,迷失于毒品中。所以我们时刻记住自己不过是普通人,保持谦卑很关键。 5. 《火中飞蛾》里的火指的还有手机、电脑这些,你看现在每个人都在“扑火”:“看看我,看看我!”到处都是自拍,每个人都想在facebook上多要一些“like”,或者去证明“我比你的粉丝多,我更重要”。 6. (玩乐队)比婚姻可难得多了!在婚姻生活里,假如什么都出现了问题,至少还有性爱做补偿。可玩乐队呢⋯⋯也许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就最像性爱了。演出时所有人都充满了高潮,就像是磕药了那样。无论我们之间出现了什么摩擦,在台上时都会立刻治愈。 就像人们说的,婚姻里两人吵架,吵得差不多了就做爱,这能很快把局面缓和下来,可是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我们不想把自己弄得这么廉价,所以通常我们还是会坐下来,不光是要暂时止血,还要彻底把问题解决掉。所以沟通是最关键的。
2017年9月10日,巴黎,AccorHotels Arena体育馆。重金属乐队Metallica正在为乐队的第10张专辑“Hardwired...to Self Destruction”做世界巡演。这是巴黎巡演的第二天,场馆内座无虚席,靠近舞台的站立席更是像下饺子一般,挤满了从法国各地赶来的乐迷,没有一丝缝隙。演唱会还没开始,从坐席到站席上的乐迷自发伴随着“me-ta-lli-ca”的呼喊声,做起了人浪“wave”。伴着一波高过一波的呼喊,Metallica 四位成员从观众席的四个方位中冲上舞台,一首首大合唱响彻场馆。 无可否认,Metallica是史上最成功的殿堂级重金属乐队。 这支以加州为大本营的重型乐队不仅帮助曾经的“地下之声”登堂入室,更以独特的快速节拍和大声量与Slayer、Anthrax和Megadeth并称为thrash metal的“四大巨头”,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已卖出了超过一亿一千万张唱片;乐队多年来还以与不同领域的音乐人跨界合作著称,曾与Lou Reed、Lady Gaga、郎朗等音乐人在格莱美等多个舞台上合作。 这一切都开始于乐队鼓手Lars Ulrich于1981年在报纸上登的一则广告:“寻找金属乐手一起玩乐队”,主唱James Hetfield 写信回复。后来Lars接受了一个朋友的提议,给乐队起名为“Metallica”。 Metallica是一支四人乐队,但事实上主心骨就是两位创始成员:主唱兼节奏吉他手James Hetfield和鼓手Lars Ulrich。乐队的贝斯手和吉他手都曾有更换,唯独这两人至今拆不散。 接触过就知道,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James 是从小到大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美利坚之子,36年如一日地写下“毁灭”“死亡”“救赎”这样的歌词,释放愤怒和内心的黑暗。Lars则是硬币的另一面。他出生于中上阶层的丹麦布尔乔亚家庭,从小就被往职业网球手的方向培养,还有爵士乐大师Dexter Gordon当他的教父。他说,“愤怒”“叛逆”从来没在自己的字典里出现过。 巡演前的下午,乐手们轮流参与到《时尚先生Esquire》杂志拍摄。当换上了剪贴合身的西装的James坐到镜头前时,陡见他眉头紧皱,双手别扭地放在领子上,像极了一个随时要逃离现场的少年。西装几乎遮住了他全身的刺青,但还能看见文在他手背上的字母M和F:一个是乐队名的首字母,F则代表了James的阿根廷爱妻Francesca。James不止一次公开说过,结婚以后慢慢学会了收敛自己的暴戾脾气;2001年下定决心接受治疗,戒掉了曾经长期困扰他的酗酒、毒瘾,也归功于妻子的不屈不挠。 过了10分钟后,James脸上的线条逐渐柔和,到上天台拍视频的时候,James已纯熟地做出硬核摇滚标签式的夸张狰狞表情。这时一阵冷风吹来,James裹紧了上衣,忽然扭头望向远处自语:“冬天要来了。”第二天在促膝专访中,这位硬汉不止一次对自己和听重金属的乐迷与世界的关系用上“格格不入”来形容。他不断抽离的状态,此时就显得合情理了。 相比之下,Lars似乎更容易放松一些:他主动握手,主动拉家常。可在问答之间,Lars冷不丁会指向摄像人员:“看他,多紧张!”然后自顾自大笑起来。类似这样毫无征兆的小插曲发生了两三次以后,忽然令人意识到,狡猾的Lars也许是在有意无意地玩心理学上的把戏。别忘了直到2004年,Lars还因为上台之前太紧张而导致全身痉挛,不得不被送往医院,缺席了那场演出。 Metallica每巡演到一个城市,都会留出三五天时间自由活动。自称偏爱“抽象表现主义”的Lars,每次到巴黎都会去画廊和博物馆看展。他喜欢巴斯奎特,也会坚持将安德列斯·塞拉诺的受争议画作用到乐队的唱片封面上。这次,这位十足的欧洲“布尔乔亚”还是在左岸待得最长,与太太逛街、看电影、下馆子。一天下来先后碰到10个路人要求和他自拍,Lars也来者不拒。 1991年乐队凭借第5张同名专辑“Metallica”(又名“黑专辑”)首次登上美国“告示牌”排行榜第一名,自此后乐队的每一张专辑都获得过同样的成功。Lars认为Metallica是在音乐创作上不妥协的前提下获得了商业的肯定,他们对名气的接受毫不拧巴。按Lars的说法,并不是Metallica往主流靠,而是主流世界朝Metallica靠拢。 2017年9月10日 法国巴黎
Esquire(以下简称“ESQ”):你在一次采访里似乎表达过古典音乐有点僵化,比不上摇滚乐那么随性? James Hetfield(以下简称“JH”):哈哈。古典音乐就是一切啊:要宁静有宁静,要能量有能量,有时也令人精神紧张,它能唤起各种情绪。但我听不了太久,久了就会觉得很闷。 跟交响乐团合作时,我挺害怕的。我觉得低人一等,因为我不会看谱子,和弦的名称我也说不全,我只是就这么弹。做乐队以来,识谱这些并不重要,所以我感觉自己没准备好,人家才是真正的音乐家。幸好乐团里面除了少部分势利眼以外,大多数人的心态很开放也很有爱,对我们很欢迎。有人会对我们说:“嘿!我家孩子觉得你们玩的音乐酷毙了。”我记得弹竖琴的音乐家,在他的燕尾服下面是一件Metallica的T恤,T恤下面则是文身。他平常都是骑辆摩托到交响乐团来上班。 ESQ:Metallica参与这种跨界项目时,是有吸引新乐迷的愿望,还是纯粹觉得好玩? JH:我们想拉拢一帮古典乐迷,然后把Metallica的唱片卖给他们?当然不是。对我们来说,只是去探索不同的音乐形式。曾经有过不少记者问我们为什么想到要跟Lou Reed合作,毕竟我们那么不同。可我们一点儿都不这么觉得。Lou Reed同样无所畏惧,他是个纯正的叛逆者,摇滚起来谁都不输。 ESQ:你也是个叛逆者吗?“重金属”这个称谓从1968年由一位记者开始使用到现在,在你看来,这个音乐风格有过什么革新或改变? JH:哈哈,我算叛逆吧。叛逆性格对玩摇滚确实有帮助。“重金属”这个标签,对我们来说,一直都有点太局限。重金属的乐迷曾经对我们很生气,因为我们经常不按规矩出牌:把头发剪短了,不穿重金属乐队应该穿的那种服饰,忽然间出了一首抒情慢歌“Nothing Else Matters”—— 哇,乐迷都炸锅了:“不要不要不要!”我们不在乎,真不在乎。我们的音乐是为自己写的,这是天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所以我们算是叛逆者中的叛逆者吧。 Lars Ulrich(以下简称“LU”):在硬摇滚的圈子里有一派保守势力,他们就要做从包装到内容都符合硬摇滚的东西。可我们从来都觉得这样不舒服。我们有好奇心,喜欢探索音乐的新世界,我们只往内心找答案,想怎么做音乐就怎么做。Metallica的音乐来源于生活,一幅画、一部电影、一本书,我们的孩子、父母,都是继续创作的灵感所在。你看,35年前我们在第二张专辑中加入了箱琴,许多硬核金属迷也对此很不屑。可以说我们是在硬摇滚、重金属圈子之外的,他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太杂,不纯粹。可我们谁都不欠。 ESQ:你会称之为革新吗? JH:我会称之为自私。我们写自己想听的音乐,因为我们无法在别的地方听到。这么说也不完全对,我们不时会听到喜欢的东西,就会这里那里收集一些,吞咽下去,消化一下,最后排泄出来就是Metallica的东西,哈哈哈哈! 每一种音乐风格,古典乐也好,爵士乐也好,有些人就是被它们打动,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原因。而我们喜欢的是更有侵略性的音乐,喜欢这种让我们感到有生命力的风格。我一向以来都被重金属或者说重型摇滚所牵引,我知道外面有些乐迷跟我们是一样的,因此我们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而“重金属”这种音乐,至少在美国,人们总是认为是年轻人的音乐;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了。我们一直都在进化,在成长,在改变。进化很重要,我们现在的音乐肯定跟1983年的时候不一样,我是不会一遍一遍去画同一幅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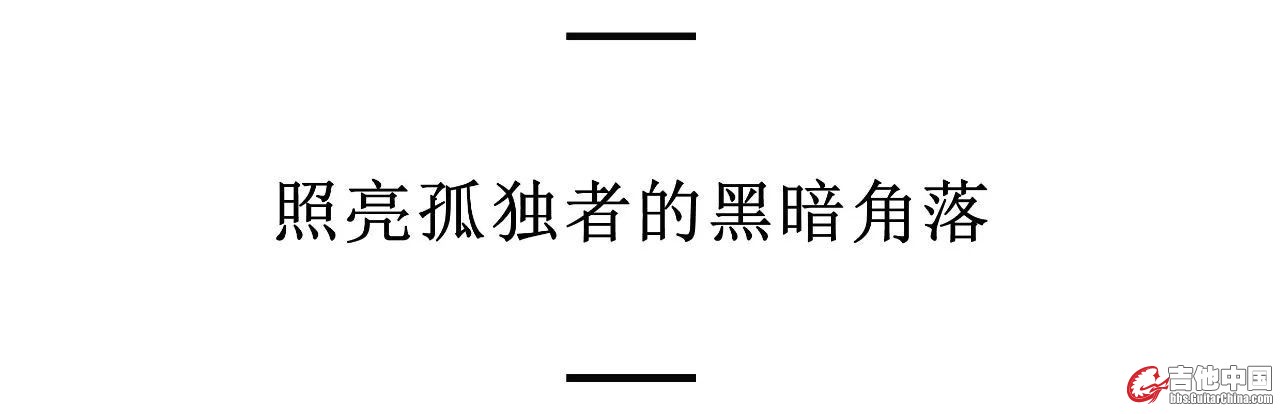
ESQ:愤怒是你们的音乐创作之源吗?如果是,青春期过了以后,哪来那么多的愤怒? JH:愤怒一直是我们写音乐和歌词的强大燃料,Metallica的能量所在。这是一种我从小就不断需要面对的情绪。愤怒从哪里来?我自己没有答案,否则我会好过一些。但无论如何,愤怒亦敌亦友,它是我的一部分,我很早就接受了这个事实。这并不意味着我被愤怒牵着鼻子走,它只是我的一种生存工具,但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,也没有以前出现得多了;我也不会再把身边的人都赶走。 ESQ:重金属音乐一般给人的印象恰恰是自我极大:歌词大多是自我愤怒、压抑的宣泄,你是怎么被重金属吸引的呢? LU:硬摇滚、重金属音乐,就跟其他任何一种类型音乐一样,总是存在固定的标签,人们对这些标签也总有定见。但对我来说刚好是反过来的:我总是能够在重金属音乐里找到归属感。我是家中的独生子,从小就有一种孤单的感觉。而在摇滚乐里,我能够和其他人联系到一起。不论种族肤色文化差异,人的基本需求就是与他人连接,不要疏离。 而James跟我是完全不同的人,他的成长与父母比较疏远,有时候他写歌词的时候就是在释放自己的内心困扰。话又说回来,描写愤怒和忧郁的音乐并不局限于重金属,我个人并不赞成墨守陈规,因为世界在我们眼中并不是非黑即白,在我眼里,黑白之间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。 ESQ:与许多金属乐队相似,Metallica的词一向黑暗:死亡,自杀,毁灭。这些会随着年纪而颠覆吗? JH:黑暗将会是我们永恒的主题。我们喜欢做的是在漆黑之处洒下光芒。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,我喜欢去照亮黑暗的角落。感觉到黑暗不是我们的选择,但有时候它还是会袭来。据我所知,许多Metallica的乐迷,或是出于恐惧,或是出于对家人和朋友的需求而对我们的词产生共鸣。联系人心是最重要的事。我把自己怎么想的写到歌里,外面听到的人也有共鸣,同样是在社会中格格不入的人,便不再感到孤独。 ESQ:回忆起1991年你们在俄罗斯的演出,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 JH:当时柏林墙刚刚倒下,我们能够走进铁幕背后,在一个飞机场上演了一场免费音乐会,举目所望全是人,没有人知道到底来了多少人。最开始,我心里挺害怕的,因为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告诉我们俄国是敌人,俄国人是坏人。而现在我们却到了“敌营”,感觉实在太奇怪了,到处都灰蒙蒙的。到红场去的时候,我紧张得坐在车里不敢出来。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开始跟当地人说话,发现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两样。到了音乐会上,就只有喜悦了。我们都松了一口气,暂且忘掉核武器吧,那天我们都很尽兴。我们并不是一个政治乐队,但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,很有意义。
ESQ:Metallica成军36年,牢牢维系住乐队、无法拆散你们的是什么? JH:这么想起来,我们好像已经过了好几辈子了。尤其是在我们各自都有家庭以后,怎么去平衡乐队巡演和家庭事务,就成了最棘手的环节。尽管我们很清楚乐队四人性格完全不同,同时我们也知道大伙儿在一起工作极为默契。比如说,一个问题出来,我们一定会有各种截然相反的答案,大家对此心知肚明就很好。意见完全相反时,我们得找到折中点,而不是我想方设法把他人打倒以达到我想要的。矛盾这东西其实是充满能量的,正是因为太在乎、太热爱才会产生,矛盾,它能释放出激情来。如果完全没有矛盾才令人担心。 LU:我们能走这么远,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给彼此许多空间。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玩乐队很容易,乐队可以是放在第一位的;但到了50岁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生活,家庭成了第一位,乐队成了一个机动的组织。也因为这个原因,一般都是年轻人组乐队,年纪大了就单飞,因为没人愿意妥协。所以我们花了大力气去确保每位成员的私人生活时间,大家都开心,乐队才有可能走下去。 ESQ: Lars,Metallica1996年发行的专辑《Load》封面用的是美国艺术家Andres Serrano受争议之作《精与血》,据说那是你喜欢的抽象艺术,但James并不喜欢。 LU:在Metallica、U2这样的乐队里,乐队成员轮流做决定,有时候我对某样事情特别激动,乐队其他人就会妥协:那好吧。这件事对其中一个人特别重要的话,其他人就会让步。这跟一场婚姻没什么区别,有索取也有给予。 JH:(玩乐队)比婚姻可难得多了!在婚姻生活里,假如什么都出现了问题,至少还有性爱做补偿。可玩乐队呢⋯⋯也许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就最像性爱了。演出时所有人都充满了高潮,就像是磕药了那样。无论我们之间出现了什么摩擦,在台上时都会立刻治愈。 就像人们说的,婚姻里两人吵架,吵得差不多了就做爱,这能很快把局面缓和下来,可是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我们不想把自己弄得这么廉价,所以通常我们还是会坐下来,不光是要暂时止血,还要彻底把问题解决掉。所以沟通是最关键的。 ESQ:你们之间最不可收拾的摩擦是什么? JH:最严重的就是彼此都不愿意再继续合作下去了。这样的局面一点儿都不少见,几乎每做一张专辑我们都说过这样的话。恰恰就像在婚姻里面,一个人说出了最致命的那句话: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,我想要离婚!然后另一个人听了就会心里面一紧。这样的时刻,谁都不想再妥协,谁都不再向对方敞开心门,让他们感受自己的痛苦或自由。 我们都是创造型的人,内心里怎么都会有一点儿不安全感,“自我也很大”。自我和不安全感合在一起,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某一天你会感觉什么事情都糟透了,过了一天你又会忽然觉得一切都很顺。就这样,像过山车,充满了起伏跌宕。 当然了,在我们做《圣徒愤怒》这张专辑之前,拍了一部纪录片叫《Some Kind of Monster》,这部片子的拍摄期间,应该是Metallica成军以来的最低潮。当时我们的摩擦和矛盾全都被拍下来了,整部片子就像一面直视我们的镜子,直接照进了我们的内心,促使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反思了作为一支著名乐队的乐手的困境,还思索了生活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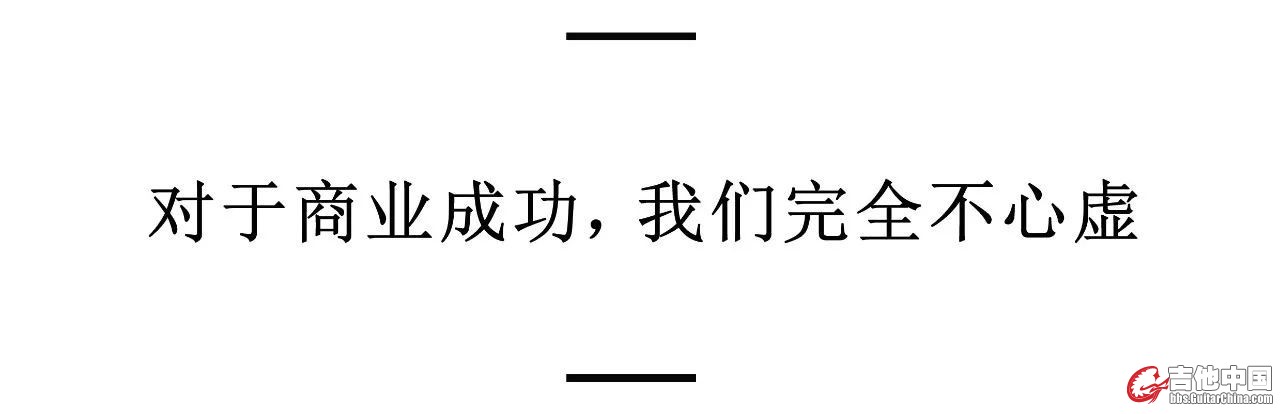
ESQ:对于商业的成功,你们介意过吗? LU:我可以直视每个人的眼睛说:我们完全是凭借自由、自我的创作去获得商业成功。我们的音乐道路走得很纯粹,因此对于成功,我们完全不心虚。与其说Metallica向主流靠,不如说是主流向Metallica靠拢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中部,那时候进入青春期的小孩还极少有机会听得到我们这种音乐。当我们的唱片卖得越来越多,也就有更多的唱片公司愿意发行金属乐,知道我们、知道金属乐的人数也越多。这是好事。 ESQ:新专辑中的《火中飞蛾》(Moth in the Flame)与金钱和名气有关。你们怎样区分摇滚巨星的身份与真实人生? JH:“摇滚明星”这个称谓,从人们口中说出来,经常带着贬义。对我们而言,没错,我们有点才华,会写歌会玩乐器,但换作是另一个人,同样可以做到。我们牢记的是:我们不过都是乐迷,只不过组了一个乐队,并能由此去连接大众。如此而已。在家里,我就是孩子他爸,我太太的帮手,白天开车送孩子去上学,倒垃圾,洗衣服,捡狗屎。而在巡演的路上,这一切都有人打点。在家和在路上,这种过渡不容易。 在《火中飞蛾》里,我写到了“名气”之下的众生相。包括美国人一项著名的消遣:先将你捧上天,再把你乱刀砍倒,看着你从高空坠落,真是精彩得没朋友。又或者是削尖了脑袋要把别人家长里短打听个一清二楚,好装成道德义士去指指点点。真是令人受不了。当然了,在各种艺术领域里,像Amy Winehouse这样的遭遇已经重复上演了无数次:你追寻的是明亮而真实的人生,但人们将你捧到了一个不可能的高度;于是名气逐渐毁掉了自我,迷失于毒品中。所以我们时刻记住自己不过是普通人,保持谦卑很关键。 对了,《火中飞蛾》里的火指的还有手机、电脑这些,你看现在每个人都在“扑火”:“看看我,看看我!”到处都是自拍,每个人都想在facebook上多要一些“like”,或者去证明“我比你的粉丝多,我更重要”。 ESQ:你如今有什么样的恐惧或担心是连“摇滚巨星”的光芒也挡不住的? JH:我最大的恐惧应该是再也不能写音乐、玩音乐、演出了。即使我们变老了,没法继续频繁巡演了,但艺术家是没有退休这种事的,(音乐)就像呼吸一样,是我们的生命所在。就算Metallica有一天不存在了,保持写音乐、演出依然重要。
| 